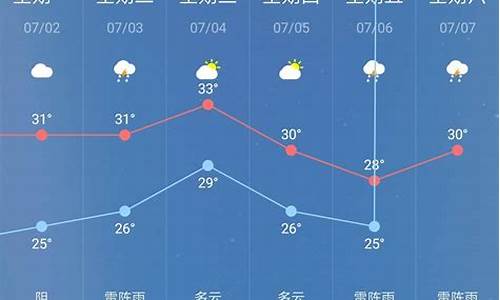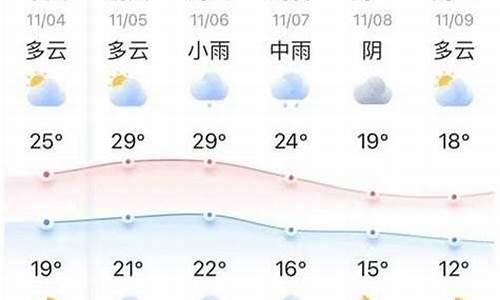1.脑瘫儿进哈佛29年前妈妈只要他能活着是怎么回事?
脑瘫儿进哈佛29年前妈妈只要他能活着是怎么回事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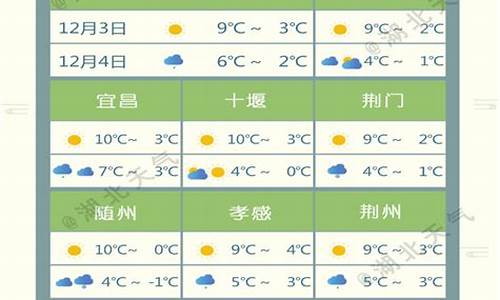
有一次,去按摩的路上遇到大雪,我骑自行车带着儿子不小心滑进了水坑里。我把他扶起来,自行车倒了,把自行车扶起来,他又倒了。等把他抱上自行车,走到医院,已经成了泥人。
2015年7月,邹翃燕参加儿子的研究生毕业典礼。
邹翃燕埋藏了29年的秘密被揭开了。
母亲节后一天,她将脑瘫儿子送进哈佛的故事,登上了微博热门话题。
29年前,儿子丁丁(第二个丁读zhēng,记者注)因出生时宫内窒息,被医生判了死刑——“不是傻就是瘫,建议放弃”。母性本能驱使邹翃燕做出选择。她决定赌一把。“我只要他能活着”。
这二十多年,丁丁的身体缓慢恢复,从外貌上已经和正常人没有区别。十年前,他考上了北大,再过几个月,他将从哈佛毕业。
5月16日上午,这位54岁的母亲说起29年前的生死抉择、独自一人带孩子的艰辛,以及生活给予她的重击时,语速轻快,云淡风轻。说到儿子一点点的改变时,不时笑出声。
作为单亲妈妈,她没法去跟别人诉说这其中的痛苦。“说了又能怎样呢?别人安慰你几句,陪你掉几滴眼泪,有什么效果呢?路还是得你自己走,日子还是得你自己过,我不是那种希望被人同情的人。”
她也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。“我只是运气不好,但我接纳了,做了我该做的和能做的。”
丁丁7个月大时和母亲在一起。
我是妈妈,我不能放弃他
1988年,我25岁,是武汉幼儿师范学校(现武汉城市职业学院)的一名老师。那一年,我做了母亲。
江城夏季炎热,7月份,我被送到荆州的婆婆家待产。
7月18日上午6时,我被送进荆州市下属的一家县级医院。那时正是医院早上交接班时间,我在产床上躺了两个小时,等医生接班,孩子已经出现宫内窒息的症状。9点30分,孩子出生。7斤6两。
因出生时出现过窒息的情况,孩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市区医院抢救。
在病床上,我很着急。四天后,第一眼看到孩子。他身上没洗干净,皱巴巴的,护士给他打针,由于血管太细,半个多小时扎不进针,护士豆大的汗珠滴在他脸上,什么反应都没有,眉头都不皱一下。旁边的小孩觉得疼,会哭,他不会。
医生说,孩子宫内窒息,曾气管插管给氧抢救,出生次日有抽搐的情况,可能是重度脑瘫,颅内有出血,但现在孩子太小,做不了CT,无法确认血块有多大。接着,她分析,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血块压迫大脑,影响认知,会痴呆;一种是压迫小脑,影响运动神经,会瘫痪。简单来说,这个孩子,要么傻要么瘫。医生下达病危通知时说,你们还年轻,以后还能生健康的宝宝。这一个,建议放弃。拔掉输氧管,几分钟就结束了。
我当时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,好像不是踏踏实实站在地上,是飘起来的,在空中浮着。医生后来说了很多,但我感觉她的声音越来越远。
在医院的走廊里,我放声痛哭。我觉得不公平,我明明这么努力,为什么厄运会降临在我头上。我是做了那么充分的准备在等待这个生命啊。
那十个月,我对着《孕期指南》的食谱吃东西,我以前从不吃猪肝,但书上说猪肝和动物肝脏对孩子视力形成有帮助,我就吃,吃了吐,吐了继续吃。我改掉了以前晚睡晚起的习惯,早上起来给他读诗,晚上睡前给他放胎教音乐,就希望他能有个好的生长环境。
那时候,我最喜欢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自传体小说《窗边的小豆豆》。我常常摸着自己的肚子和他说话:你以后是不是会像小豆豆一样可爱?你会不会比他更乖一点?不管你是男孩女孩,小名就叫“豆豆”了。
这十个月,我们虽然没有见面,但我和他有过那么多交流。我是妈妈,我不能放弃他。
医生再次征求意见时,我说我不想放弃,我只要他能活着。
我记得,当时病房里有两个特危孩子。有一天早上,我醒来时发现,隔壁床的孩子不见了,夫妻俩也不见了。医生说,他们放弃了。
我看着自己的孩子,不哭也不闹,突然想起了《诗经》里的“伐木丁丁,鸟鸣嘤嘤”。树木倒下也能发出一些声响,要是我的孩子也能给世界留下一点声音和动静就好了。我给他取名“丁丁”。
开始我是假装坚强,装久了,就变成真的了
十几天后,我们出院。回到家里,我才感觉到害怕。躺在身边的儿子,头都抬不起来,直流口水,我就睁眼看着,发呆。脑子里好像想了很多东西,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——他要是真傻,怎么办?
孩子半岁时,我带他去医院看智力专科。他从小吃药比吃饭还多。但一直无法确定智力是否存在问题。但他三个月大时,我给他看彩色气球,从他眼珠子的转动来看,他好像是可以分辨颜色的。我很兴奋,那会儿就觉得,他至少是不傻的。
他八个月大时,医生确定,这个孩子智力没问题。但当年的宫内窒息还是给他留下了后遗症。医生的诊断是,智力正常,但左轻偏瘫,左脚活动不灵,走路不协调,有运动障碍。
别的小孩两岁就能走,他不行,只能扶着摸索,抓力和握力都很差,3岁才学会走路。我一边在家里帮他训练,一边带他去医院做康复按摩。
丁丁三岁时学会走路。
对他来说,写字和用筷子都是非常痛苦的经历。别的小孩轻而易举完成的事情,他要花费几倍于别人的时间。为了训练他的握力,我和他比赛撕纸,用了一年,他才能撕出花样。他握不住笔和筷子,我就和他比赛递东西,直到他能拿稳重物,又是一年。
我每周要带他去做三次全身按摩。每次一小时,晚上七八点过去,六七个人围着他,按手、按头,按脖子,最后一个步骤是揪起背上的皮,一点一点碾。很疼,其他小孩哭,家长跟着哭,家长一哭,孩子哭得更凄厉。
最开始,丁丁也哭。我跟他说,你哭了就不疼了吗?如果哭了不疼,那你使劲哭,我也帮你哭。如果不是这样,咱们就不哭了。
后来我就看着他在病床上,咬着牙不哭,吸鼻子,哼哼。我心里很难过,知道他疼,但还要跟他开玩笑说,背上卷皮都卷出一朵花来啦。
有一次,去按摩的路上遇到大雪,我骑自行车带着他不小心滑进了水坑里。我把他扶起来,自行车倒了,把自行车扶起来,他又倒了。等把他抱上自行车,走到医院,已经成了泥人。
孩子10岁那年,我和丈夫离婚,但从儿子上幼儿园,我们就在谈离婚。分歧在当年决定要不要抢救儿子时就有了,他主张放弃,我不同意。后来他跟我说,以后孩子你养。我当时就赌气一样说,我养就我养。
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太苦,又没有精神支撑。我会问自己,值得吗,犯得着吗。有一回,他半夜起来上厕所,卧室门反锁了,我从7楼阳台翻进他卧室,把门打开。十几分钟里,整个人是瘫软在地上的,要是我从楼上摔下去怎么办呢?那时候就想,如果我撑不下去,就带他一起走,没有我,他怎么活。
有一回,我晒洗枕套,发现白布里面有褐色斑点。儿子问我这是什么。后来想想,可能是泪痕,做梦时无意识哭,留下来的。有时候真得太焦虑了。
我没法去跟别人诉说这种痛苦。说了又能怎样呢?别人安慰你几句,陪你掉几滴眼泪,有什么效果呢?路还是得你自己走,日子还是得你自己过,我不是那种希望被人同情的人。靠同情没法过日子,还不如不哭。
其实开始我是假装坚强,因为我儿子需要我,我不坚强,儿子怎么办。装久了,就变成真的了。儿子这件事,我真的在乎,真的难受,但我假装不在乎,不难受。摆在面前的坎,等我闯过一次、两次,回头再看,我发现,我还挺能干的。
丁丁和母亲邹翃燕。
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个苕?
我自学了家庭按摩。他放学回家,我就帮他按摩。
他在一点点恢复。上小学时,学校离我们家步行十来分钟,他走起路来,左腿还是没劲,耷拉着,比正常人慢。一个绿灯的时间,他过不了马路,红灯亮了,他站在斑马线上,朝来往的车辆示意,车都会停下来。
小学时,每次考试,因为他写字慢,我得跟老师申请给他延时。四年级以后,他的速度也逐渐跟上了。我们有个策略,做过的部分要保持正确率,这样的话,即使答不完题,也能有很好的分数。
邹翃燕近照。
我最担心的是身体原因会让他产生自卑心理。他小时候,我给家里买了很多玩具,吸引大院里的小孩儿到家里来和他一起玩,毕竟他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去跑去闹,医生说,如果发生冲撞,再伤到头,就前功尽弃了。
我用让他复述《天气预报》和《新闻联播》的方式去训练他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。小学低年级时,他喜欢跟大人们讲新闻里看到的东西,讲苏联解体。大人们都表扬他。这无形中增强了他的自信。
初一时,我试着让他去参加军训,融入集体。但提前也给老师打了招呼,如果他做不到,希望教官不要批评他。向左转,他慢半拍;抬腿、正步走,他也不行。教官从没批评他。别的孩子有意见了。教官就说,人家是脑瘫儿。后来同学们编顺口溜骂他,“丁丁是个苕(武汉方言“傻”的意思,记者注)”。
他给我打电话说不想上学了。我当时正在贵州学习,坐了30个小时火车赶到学校。课间10分钟,我走到讲台上,跟孩子们说了丁丁的情况,还跟他们说,如果上天不眷顾你,让你身患疾病,你已经很痛苦了,还遭到辱骂,你不难受吗?我声音是有些哽咽的,孩子们可能被这样的场面震住了。全班寂静无声。
出门我就跟儿子说,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个苕?退学能证明吗?不行,你只能靠优异的成绩来证明自己。
后来,他的成绩一直都在年级上游。
我年轻时的心愿就是读北大,只是后来上了湖北大学中文系。他刚懂事时,我跟他说,北大是我非常想去的地方,你要帮妈妈完成心愿。他说,你放心吧。后来,他真的以660分考上了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。
2015年7月,邹翃燕在儿子的毕业典礼上。
接到通知书时,是个傍晚。我看到那张白底红字、写着“北京大学”的录取通知书,眼泪真的要掉下来了。他倒是挺冷静的,一直在担心到北大去学习跟不上了怎么办。
本科毕业后,他又被保送到北大国际法学院。这次换专业也和他的身体有关系。尽管他现在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差别,但很多精细化的工作还是没法完成。比如,他无法控制手指的力度,往试管里滴试剂,有时候多了,有时候又少了。别人一天能做两场实验,他可能一天都待在实验室里,也做不完一个。
哈佛是他毕业、工作以后申请的。他原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法务,但感觉职位太过边缘,想继续读书,就申请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LLM(相当于国内的法学硕士,记者注)。其实只有一年的课程。去年夏天去的,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了。
原来这样的家庭有这么多
儿子的事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坎了,我已经跨过去了,其他的困难,对我来说已经云淡风轻。明年我也将送走我的最后一届学生,享受退休生活。
有人说我给了儿子两次生命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没错的,当年要是我签字,他就没有命了。他自己也说,我是他的精神导师,亦师亦友。
丁丁20岁时的照片。
有人问我,如果儿子没有考上北大、没有进哈佛,只是平庸之辈,我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和付出。我真的不后悔,我的初心就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,能有所作为更好,从没想过一定要他上北大。
丁丁考上北大以后,身边陆续有同事、朋友知道了他的状况,介绍了一些有脑瘫儿的家庭给我。我才发现,原来这样的家庭有这么多。以前我只顾自己,觉得自己是个案。那时候才发现,原来大家都找不到方向,迷茫,甚至很沮丧、痛苦、失望。
我跟儿子商量,能不能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,给同样境遇的孩子和家长一些鼓励,让他们有信心走下去。治疗总比不治疗要好,多一些坚持,少一些放弃,这些孩子或许都能成为可以自立的人。
我儿子同意了。我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。
很多家长来加我微信、QQ,有语言发育不好的,脑积水的,都来问我,他们应该怎么办。我给不了他们切实的帮助,真的,我不是医生,怎么治疗,我也不懂,只能跟他们说,到医院去,坚持治疗,自己可以主动学习一些按摩方法,这才是积极的态度。
作为母亲,我也理解他们。他们可能也没想从我这里得到专业帮助,只是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吧。
现在医学水平比二十多年前高很多了。我不能说坚持一定会有奇迹发生,但坚持总比放弃好。放弃治疗就是放弃了希望,放弃了孩子的未来。
我总会想到当年曾和丁丁一起做按摩的一个小男孩,因为太疼,那个小孩坚持了一个月,没有再去了。后来碰到他家长,说他只能待在家里,行动依旧不便。